保罗在旧金山湾区打零工,他原本是一名科技行业的项目经理,但接连被几家公司裁员。他目前在来福车(Lyft)、优步(Uber)和任务兔子(TaskRabbit)等服务平台接活。虽然勉强能维持生计,但这些工作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。
“老实说,很多时候我工作时,顾客甚至不知道我的名字。即使我说了我叫保罗,他们仍伸手一指,然后说‘好,东西放那儿就行’。我把东西放下后,他们毫无表示。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动化的,我也只是系统的一部分。”朋友和我说,你现在本质上就是一台自动售卖机。
对于保罗来说,这种“隐形感”令他感到痛苦。“我不想成为机器人。我想要拥有某种……”保罗暂停片刻后说道,“跟人说说话,能让我开心得多。”保罗的挣扎反映了一种名为“孤独危机”的当代症状。

电影《坠落》中,主角作为仓库搬运工,在庞大的物流中心工作。
人们对孤独有着普遍的担忧,科学家将其定义为个人对社交需求未被满足的状态(他们区分了孤独与社交隔离,前者是主观感受,而后者是客观的社交联系数量)。2023年,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宣布孤独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病,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了“社会联结委员会”,并将其认定为“全球公共卫生优先事项”。英国和日本的政府甚至设立了“孤独事务大臣”。在全世界范围内,孤独问题已经引起了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的高度关注。
得益于研究,我们对孤独有了更多认识。首先,孤独问题严重影响健康。研究表明,孤独和社会隔离会增加死亡率、痴呆和中风的风险。对成年人而言,孤独与心脏病、肥胖等慢性病相关,并且会降低工作表现和投入程度。孤独的少年儿童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、游戏成瘾,或遭遇睡眠障碍。此外,孤独还会影响学习成绩,孤独的孩子也更可能辍学。
毋庸置疑,孤独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都有不良影响,但其成因却颇具争议。科学家对屏幕使用时间和年龄是否对孤独造成影响意见不一,对于孤独是否增加也尚未达成共识。尽管孤独问题确实重要且普遍,但这场所谓的“流行病”并不新鲜。长期来看,老年人的孤独感趋于稳定;而过去五十年里,年轻人的孤独感呈现缓慢的小幅上升。根据澳大利亚政府的数据,尽管各年龄组存在差异,但15岁以上的人群感到孤独的比例与20年前相似,约为15%。甚至疫情对社交关系也没有像预期中那样,造成毁灭性打击。最新研究表明,总体而言人们的聚会习惯和密友数量在疫情期间下降,但随后又回复至疫情前的水平。虽然孤独确实严重损害健康,但我们可能并不比过去更孤独。
专家和政策制定者用“孤独”一词来描述这个真实且日益严重的问题,但他们的判断有误。他们所谓的“孤独”,其实是另一种危机:去人格化(depersonalisation)。当人们感到的不是单纯孤独,而是不被看见的“隐形感”时,去人格化就产生了。这里缺失的是学界所说的“被承认”、“被在乎”或“被看见”的感觉——即你是否被其他人真正看见、听见,甚至能在情感上被理解,而不是感到自己无足轻重、如同隐形。
去人格化危机反映了我们对关注的供需变化。匿名性早已成为现代化社会的诅咒,这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等长期趋势密切相关。但即便是在当代发展中,某些现象依然强化了这种感觉:例如服务业中标准化的扩张——就像杂货店收银员机械地问“纸袋还是塑料袋”,或者客服赶在你电话挂断之前抓紧说完结束语,这些都会让我们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编号。与此同时,尽管婴儿可能对“受到关注”有基本需求,但如今人们认为他人理应给予自己情感认可,这其实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观念。这表明了治疗文化的兴起,以及什么才是“合格的育儿”所经历的变化。当保罗满怀期望地说到自己不想成为机器人,或谈到顾客指指点点、让他把货物放在哪里时,他谈论的正是去人格化。
生活在“不够重要”的状态中
莎拉是一家退伍军人医院的心理治疗师,她告诉我,“去人格化”如何在她的临床实践中引发了一次关于“错误”的力量,令人惊讶的顿悟。她曾经有一位病人,是一位在军中经历过性创伤的女性。莎拉讲述说,大约在第三或第四周的治疗结束时,那位女性离开时提到自己“可能会很忙”,可能无法继续来治疗。“好像哪里不对劲,”莎拉回忆说,“感觉和平时不太一样。就是觉得不太对。”所以在下周见面之前,莎拉给她打了电话,告诉她自己觉得有些不对劲。莎拉大概是这么说的:“今天的会谈感觉不太一样。我在想是不是我遗漏了什么,或者哪里没听明白。如果你还能再来一次,我觉得我们可以聊聊这个问题。”
莎拉说,“那一刻后来变得非常关键。她最后又来了,我们确实谈了这件事,从那之后我们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转变。她后来成了最稳定的来访者之一,那一年她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。”
治疗接近尾声时,莎拉问这名病人觉得什么对她最有帮助。她说:“有一次你注意到我对你做的某件事不太高兴。你居然察觉到了,这本身意义重大。”实际上,正是那次关系的裂痕,以及莎拉试图修复它的努力,反而加强了她们的联系。事实上,莎拉说,这样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源于来访者本来就没有抱太高的期望。她似乎一直生活在一种“不够重要”的状态中,习惯于被误解,也习惯那些从不真正留意她的治疗师。
“我觉得她是那种一生中大部分时间自己的需求都没得到满足的人,她已经习惯了,觉得别人既不会理解她,也不会注意到她的情况。所以,当有人能敏锐地察觉到她有些不对劲,并主动提出来时,那种经历对她来说非常有力量。”当莎拉纠正了自己的错误,她冲破了那层去人格化的迷雾。
有大量证据表明,许多人很少“被看见”,就像保罗和莎拉的患者一样,成为带着“去人格化”创伤行走的隐形人。在许多国家,被忽视感引发了工人阶级的愤怒。这或许是特朗普在2024年秋天赢得美国大选的原因之一。一项分析特朗普演讲的研究发现,他通过系统性地肯定工人身份的价值来吸引该群体;而在2024年大选之后,《纽约时报》的一篇专栏文章写道:“选民对精英问道:你们现在看见我了吗?”研究还表明,低收入人群更有可能感到被孤立和抑郁,并因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受到歧视,有些人甚至因自我怀疑而选择自我隔离。
尽管工人阶级和贫困群体可能更多地被忽视,但如今每个人都正在经历一种新的被剥夺感:被他人收集数据、与聊天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代理进行机械化、标准化互动,影响着各个阶层的人。去人格化已经降临到所有人身上。
当我们感到隐形时,就会产生一种迫切的、近乎绝望的被认同需求。而这种需求往往投向那些“职责”本该是去看见他人的工作者。旧金山湾区一家社区诊所的初级保健医生珍娜说:“我的病人就像在对任何倾听者唱着海妖之歌,因为没人愿意真正照顾他们。”她告诉我,她的病人会疯狂吸引她的关注。“他们习惯了需求得不到满足,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。”
珍娜说,他们的渴望如此强烈,如此执着,在社区诊所患者数量庞大、资源有限的情况下,她根本无法满足患者。研究人员指出,这样的工作环境助长了医生的偏见和刻板印象,让从业者难以真正看见“他人”。对珍娜来说,这种限制带来的悲剧让她心碎。她说:“患者想要从我这里得到的,远远超出了我所能给予的。”
“我不会引导患者敞开心扉,因为我没有时间。这对患者来说太不公平了,”她告诉我,“每个人都应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时间,这才是真正能帮助到他们的方式,但那样做无利可图。”
只有人类才能真正有效地见证人性
并非所有人都渴望得到关注。社会学家弗里登·布鲁姆·奥尔(Freeden Blume Oeur)在研究一所主要服务低收入黑人男孩的学校时(详见《被隔离的黑人男孩(Black Boys Apart,2018)》)发现,有些人渴望得到尊重、获得尊严,但也有人希望“被忽视”。这种愿望在那些曾与刑事司法系统有过正式接触的男孩中尤为强烈。对他们而言,保持相对的匿名就像是一种特权,是摆脱他人偏见的隐私,是一种在无需背上罪犯标签的情况下融入社区的方式。
尽管存在一些例外,但“被看见”的愿望十分普遍。这一点在流行文化中频频被提及,并且有研究支持这一观点。“去人格化”与孤独感有所重叠——感觉被忽视肯定令人沮丧,也会让人感到孤独,但它们并不相同。有证据表明,越来越多的人感觉自己被他人忽视、自己的声音没有被听见,这促成了一场未被察觉的紧急状况,一场无名者的危机。
保罗、莎拉和珍娜是我最近出版的《最后的人类工作》(2024年)一书中的采访和观察对象。在研究中,我关注人们为了与他人建立联系所做的工作,并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某种形式的“看见他人”——我称之为“连接性劳动”(connective labor)来实现有价值的成果。从帮助他人应对慢性疾病,到教他人如何写一篇论文。我采访了超过100人,其中大多数是诸如治疗师、教师或医生之类的连接性劳动从业者,并对他们的工作进行了超过300个小时的实地观察。
虽然调查能帮助我们了解某种现象的普遍性,或其与特定人口特征之间的关联,但只有深度的定性研究,才能让人们开口讲述这些故事。情感共鸣的体验涉及信息的传递与接收,有时是能被听到的言语,有时则是诸如点头、轻笑或皱眉等难以捉摸的身体语言,甚至是一种“氛围”或“能量”。我很幸运能亲身体验这些互动,聆听人们如何描述这些连接:如何建立它们、自己从中获得了什么、又希望他人能获得什么。要捕捉人际连接,这种微妙的情感联系,近距离观察和深度对话是必不可少的。
在这个有人提议用AI来完成深度访谈的时代,只有人类,才能真正有效地见证人性。
去人格化危机究竟从何而来?对许多人,答案必定是科技。全球网民日均上网6小时40分钟,对屏幕的沉迷显然妨碍了我们相互了解彼此的能力。但虽然技术负有责任,它并非问题的全部。
在加利福尼亚一家繁忙的退伍军人医院,心理治疗师卡蒂亚(Katya)为我提供了另一种答案。她的工作是筛查患者是否存在心理健康问题。医院要求她向患者提供一份仅需15分钟就能完成的问卷。这种做法迫使她与病人的互动变得“标准化”,这使她厌恶这份工作。
“我是与他们首次谈及心理健康问题的人,而我们却得填那张愚蠢的问卷,还得问他们是否有自杀的念头。我遇到过一些人在那一部分完全不想说话,”卡蒂亚回忆道,“我当时在做自杀风险评估,问到枪支那部分时,他说:‘我不想再回答了。’我当时想:‘糟糕,我和他的联系断了。’那一刻,我们之间原本建立的连接都被切断了。”
正如卡蒂亚和那位保持戒备的患者证明的那样,导致去人格化泛滥的一个主要原因,是个体被简化为一组数据。那种“被隐形”的感受,往往来自一次次标准化的互动体验——无论是作为客户、病人、学生,还是员工。这种趋势甚至蔓延到以关怀为宗旨的职业领域。诊所和公司试图将那些混乱、不可预测的、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系统化,以提升效率。但恰恰是那些“非标准化”的互动,才让工作人员和被服务的对象感觉自己是活生生的人。

电影《她》中,主角通过穿戴设备,让人工智能系统OS1每时每刻都能陪伴自己。
被监视者和监视者
去人格化可能源于生活在过度标准化的环境中,比如军队或其他大型机构,正如莎拉的病人所印证的那样。当人们身处一个社区,却并非该社区的一分子时,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。这可能是由于边缘化的身份,或刚刚搬来等原因。
华盛顿特区霍华德大学的生殖正义学者帕特里斯·赖特(Patrice Wright)讲述了科特尼的例子。科特尼是一位黑人女性,也是一名怀孕的研究生。在第一次产检时,她的妇产科医生和她说要控制体重,还提到了政府为贫困母亲和儿童提供的食品补贴计划(即妇女、婴儿和儿童营养补充计划)。这些言论让科特尼意识到:这名医生认为她正在领取相关补助,不了解基本营养知识,而且很可能会超重。事实上,虽然科特尼收入较低,但她并未领取补助,对营养知识也颇为了解,而且并未超重。科特尼感到自己被严重误解和忽视,之后便没有再回去看这位医生。赖特指出,这种明显的误识(治疗师会称之为共情失败),给她带来了压力、愤怒和焦虑。
当然,正如我们早已猜到的那样,屏幕有着重要影响——它塑造并阻隔了我们彼此所见的内容、我们被看待的方式,以及我们是否会被看到。事实证明,我们参与线上空间的方式会影响它对我们的作用。例如,尽管人们常表示与朋友和家人保持联系是自己使用社交媒体的原因,但约一半人表示这并非他们的主要动机;实际上,近40%的人表示他们使用社交媒体是为了“打发空闲时间”,这证明了社交媒体越来越多地被当作一种娱乐方式,而不仅仅是交流工具。当我们不断刷着他人的帖子,仅仅作为他人生活的观众,目睹他们的经历却未被回应时,去人格化现象便随之发生。
导致去人格化的趋势:互动和环境的标准化、边缘群体在支离破碎的社区中被排斥、作为观众,面对屏幕时间的激增,这些因素并非均匀分布。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:例如客户、患者、学生或员工,更可能面临标准化的环境,越可能遭受偏见、被排斥。虽然使用屏幕时间的增长确实影响着各阶层,但我们正将自己分为两个群体:被观看者与观看者。去人格化的趋势汇聚在一起,造就了一个新的“被忽视者的”阶层。
如果我们正面临一场“去人格化”危机,那为何人们都在谈论孤独?我认为,部分原因在于关注“孤独”, 符合那些试图向我们兜售“解决方案”的人的利益——讽刺的是,那些人恰恰是造成这一问题的始作俑者。
2025年春,Meta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·扎克伯格在推销人工智能时提及孤独话题,引发热议。在接受播客主持人德瓦尔凯什·帕特尔(Dwarkesh Patel)采访时,他表示大多数美国人拥有的朋友数量不超过三个,但却希望能拥有十五位左右朋友。“普通人想要的联系,比他们现有的要多,”他说,并暗示人工智能伴侣或许能填补这一空缺。
技术行业希望我们关注孤独问题,而非“去人格化”。当然,像脸书、Reddit论坛或Instagram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,使人们与朋友和家人的关系充满矛盾,它们一方面加剧孤独感,另一方面又可能帮助分隔两地的人们加强联系。屏幕让我们无法真正地与身边的人在场相处,但社交媒体也确实能拓展我们与远方亲友的联结。
实际上,研究人员表示,社交媒体提供了一种“社交零食”(social snacking),能让人与他人建立短暂联系,这有助于用户能在更长时间内忍受缺乏“真实”(长期或面对面)社交互动。尤其是对于潜水者和被动用户来说,社交媒体既能带来连接感,也会让人更加疏离。这也解释了令人困惑的研究发现:使用社交媒体既增加了人们对人际关系的满意度,又增加了不满情绪。就像零食无法提供能真正填饱肚子的卡路里,社交媒体的“社交零食”保证了这群渴望连接的用户不断回流,持续“进食”。
正是这种矛盾纠结的暧昧状态,让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些平台上寻求互动。而这些平台的亿万富翁所有者们,则一直煽动所谓的“孤独危机”。营销人员深知一条铁律:“推销你解决的问题,而非产品。”这句格言道出了他们的策略:在消费者购买你的解决方案之前,首先得让他们相信自己有这个问题。
或许这就是为什么Meta的研究团队曾研究Facebook对孤独感的影响,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该平台“总体上是正面的”。《纽约客》杂志最近引用了科技企业家阿维·施夫曼(Avi Schiffmann),后者的初创公司正在研发一款名为“朋友”的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,他表示:“我确实认为孤独危机是由技术造成的,但我也认为技术能解决这场危机。”
就像那些兜售女性卫生用品、教育玩具或体味除臭剂的商人一样,科技行业既在宣传一场广为流传的危机,又靠出售“解决方案”来获利。他们,已经变成了“孤独商人”(merchants of loneliness)。

电影《少数派报告》中,人类发明了能侦察人的脑电波的“聪明”的机器人――“先知”。“先知”能侦察出人的犯罪企图,所以在罪犯犯罪之前,就已经被犯罪预防组织的警察逮捕并获刑。
不在意机器的评判,但也不关心机器的看法
当我们把问题理解为孤独时,或许会认为各种各样的联系,甚至与机器的联系,都有所帮助。但当我们把问题理解为去人格化时,这种机械化的关系就让人难以接受了。当然,技术行业的从业者也在尽最大努力,显然他们意识到了人们渴望被看见的普遍需求;然而,他们的解决方案却是引入更多的数据和技术介入。
他们力推一种被称为“个性化”的策略,一种日益精细化的定制过程:利用技术手段获取数据,来分析一个人的健康史、驾驶习惯,甚至汗液成分。“个性化医疗”和“个性化教育”,更准确地来说是“定制化”,都是试图评估个人需求,并提供量身定制的建议:这类似于“被看见”,只不过是被一台机器看见。
自从ChatGPT横空出世以来,大型语言模型(LLM)将“机械化地看见”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。最近,各类聊天机器人被设计用于教学、提供心理治疗、给出医疗建议以及进行定性访谈,据称机器人在这些方面都比人类表现更好。例如,设计某款聊天机器人面试官的研究人员声称,它展现出了“认知共情”,通过后续追问来试图理解受访者,“接近于他们对自己的理解方式”。人们觉得机器人方便、相对便宜,聊胜于无,而且相较人类,机器人更少评判,有时甚至更亲切。相比之下,人类时常被各种时间限制和效率压力束缚,正如珍娜在她的诊所中所感叹的那样。
我们正身处在工业发展的一个荒谬时刻:人类忙到无暇他顾,机器却拥有大把时间。针对医护人员态度敷衍的技术解决方案,不是给予他们更多可支配的工作时间,而是推销更廉价、便捷的AI替代品。
最近一份有关聊天机器人疗法的报告颇具代表性:研究人员发现其效果参差不齐。一些用户表示,他们确实觉得机器人能理解自己。一位用户表示:“比起我的家人,这个应用程序真的把我当作一个人来对待。”但也有用户抱怨说,由于机器人不完美的倾听,令他们感到被忽视:“在我处于危机时,它的回复毫无逻辑,也与我写的内容毫无关联,这让我觉得自己没有被倾听。我知道这只是个AI程序,不是真人,但它最终还是让我感觉更糟,而不是更好。”另一位用户这样写道。即使忽视自己的是机器,那种滋味依旧会让人受伤。
在这个充斥着“共情型聊天机器人”的年代,人们很容易相信机器能完成需要“看见他人”的工作。人们相信机器人的任何不完美之处都只是暂时的瑕疵,很快就会被消除。但那些因为用户留存率骤降,而苦苦挣扎的工程师们心知肚明:真正能激发人类兴趣的,是其他人类,即便这也伴随着被评判的风险。珍娜的患者坚定地来找她,是因为他们看重她的意见,而他们之所以看重她的意见,部分原因在于她的专业知识,这也意味着他们冒着被她评判的风险。
当机器假装“看见”我们时,关键在于另一端不是人类,而是机器。人们或许不会那么在意机器的评判,但与此同时,他们也不会真正关心机器的看法。
当我问工程师彼得,人类在那些“看见他人”的工作中还具有什么不可替代性时,他说:“(做)一个真正的观众。”在他看来,机器人终有一天能完成几乎所有人类能做的事,比如在教育领域:批改作业和回答教学问题等。不过,他仍不确定人类是否“能赋予机器人足够的‘人性’,以至于你会想让它为你感到骄傲”。
然而,最重要的是,即便机器能够出色地完成这些工作,我们又为何要让它们去做呢?退伍军人医院的心理治疗师凯莉(Carrie)质疑,应用程序或智能代理能否具备她认为良好治疗所必需的 “非语言感知能力”( nonverbal acuity)。即便它们能做到,她也认为这样的发展代表某种政治选择:“即便机器能够捕捉细微差别、面部表情之类的东西,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?为了让科技公司赚钱?为了让庞大的行业继续扩张?我们为什么非得这么做?这就是我的疑问。”
“看见他人”是我们建立联结、构筑社区甚至开展民主的基础。在众多可能被“颠覆”的人类活动中,我们没理由将赋予生命意义的人际关系机械化。去人格化的危机是一种社会弊病,亟待人类干预,而非技术介入。
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,我们现在所做或未做的决定,将影响人工智能和“连接性劳动”的发展轨迹。一方面,我们正处于AI之春,人工智能如今被用来解决一些过去被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,比如:如何攻克医院中的耐药菌、如何预测地震,或者如何解读抹香鲸的语言,并在某些领域展现出近乎神奇的成果。人工智能开启了一个充满巨大可能性的新时代。
但它并非万能,我们也不该事事依赖它。尽管如此,人工智能正被用作人类“见证”的替代者,应用领域涵盖心理治疗、教学、医疗等多个方面。
我们已知AI带来了诸多严重问题:最常见的批评涉及算法偏见、监控和隐私以及造成失业。AI会将基于偏见和刻板印象的历史关联固化为系统设定,例如判刑算法预测黑人被告再次犯罪的可能性高于白人被告。应用程序会追踪亚马逊司机是否分心。人工智能将替代许多职业,比如皮肤科医生和卡车司机。这些都是值得担忧的问题。
但有一个问题,常常被人工智能批评者所忽略:人工智能对人际关系造成的冲击:这些连接性劳动,比如教学、咨询或基础医疗,是我们社会结构的情感支柱。
与其屈于“聊胜于无”,不如让人们看见彼此
用技术手段替代社会情感劳动,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:包括连接性劳动力的急剧缩减;由于学生选择让机器人代劳而导致教育体系的毁坏;人际交往的极度分化,连接性劳动成为奢侈品;以及支撑我们公民生活的“人与人之间的纽带”的丧失。工程师们试图用人工智能解决这些问题,因为他们关注的是单个患者、客户或员工。但如果不谈论技术对人际关系的影响,就无法应对去人格化危机。
解决去人格化危机,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其根源:标准化、排他机制以及过度使用屏幕时间。我们不应屈从于机械式的“看见总比没看见好”,而应努力让人们更好地看见彼此、相互了解。与其为了节省时间和成本而安排流程化的会面,不如改善培训、增加人手,让珍娜那样的人能有条件为他人提供真正有效的见证疗愈。
另一位医生露丝(Ruthie)告诉我:“对我来说,医学的艺术在于全身心投入,真正地在场。我真正热爱的是老年患者。我爱他们。他们渴望倾诉,渴望讲述故事、建立联系,这些是他们迫切需要的。如果你不去倾听他们讲述自己陷入困境的原因,你就无法治愈他们,而是在制造更多的病痛。这就是我在医学领域真正做的事情。”露丝花了好几年时间寻找合适的环境,直到她找到了自己的诊所:一个能让她以这种方式行医的地方。在我的研究中,我发现了一些诊所和学校,它们具备良好的社会架构,专门的资源,有远见的领导和强调联系的文化,正是这些因素让它们能够把“看见他人”作为优先事项。
我们还需要正视一个问题:谁被“看见”,谁却总是被视为“永远的观众”。这种不对等的关系需要被打破。玛丽亚(Mariah)曾为刑满释放人员开办专门学习商业技能的项目。她告诉我,学员们需要适应这个项目。“我们的创业者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被关注的感觉,他们会想:‘你的意思是,你只是想了解我的想法?只是想来这里投资我的计划?我们只是要谈谈我想做的事?’”这些学员对这种“被看见”的新奇体验感到震惊,他们提出的问题中流露出一种隐隐的痛苦:他们不确定自己是否配得上被别人如此关注。“所有这些都是一种‘解构’,”玛丽亚说,“尤其是对于那些在监狱里待了很久的人来说,他们在监狱里完全失去了权力。”这种解构的一部分,还意味着要在书籍和电影中为不同的声音留出文化空间,并在医疗和教育领域培训和聘用来自弱势背景的人,让他们能够参与其中,帮助他人讲述这些本不被看见的故事。
最后,我们需要阻止“看见”的机械化。在这个监管极其松散的时代,每当科技行业遭受批评,它就会以“反对进步”为由进行反击,这使得我们在该领域中很难区分哪些是有价值的,哪些则不然。但我们完全可以在赞扬新技术的某些用途的同时,对其他用途加以限制。首先,我们可以采用一个“准则”,用它来评估一项技术是否在取代、阻碍或促进人际关系。去人格化危机要求我们保持这种警惕,而我们的社会健康正系于此。
【*本文原载Aeon.cn,原文链接https://aeon.co/essays/how-might-neuroergonomics-help-us-deal-with-mental-overload,作者艾利森·皮尤(Allison J Pugh),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教授,著有《最后的人类工作》(The Last Human Job: The Work of Connecting in a Disconnected World,2024)。】
转载请注明来自夏犹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,本文标题:《没有名字的人:标准化、零工经济,算法与令人痛苦的隐形感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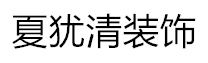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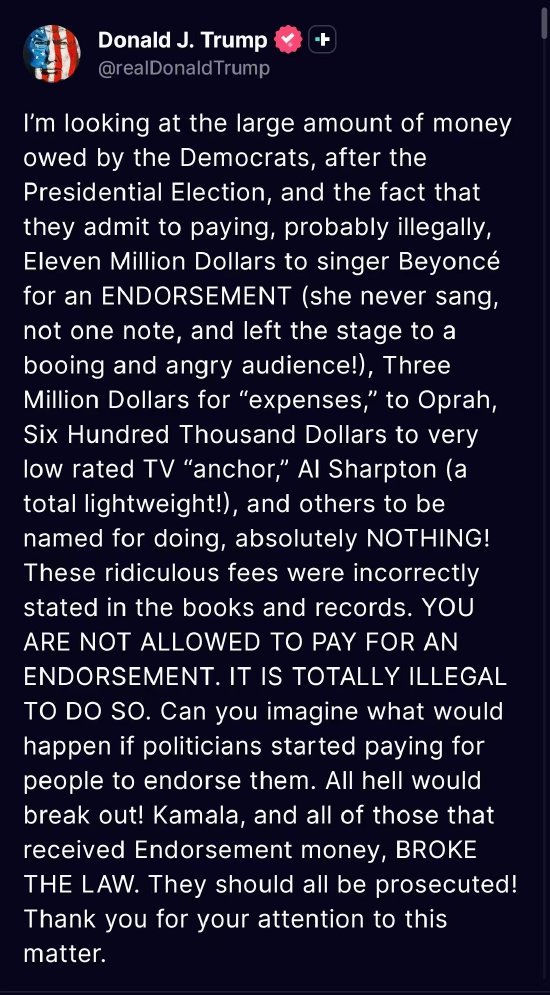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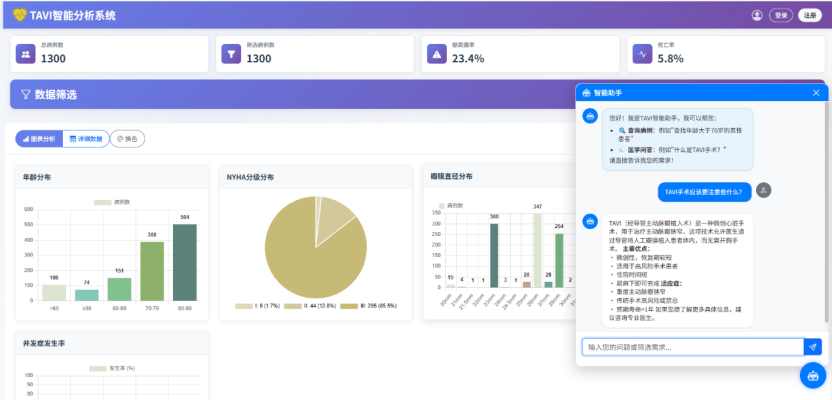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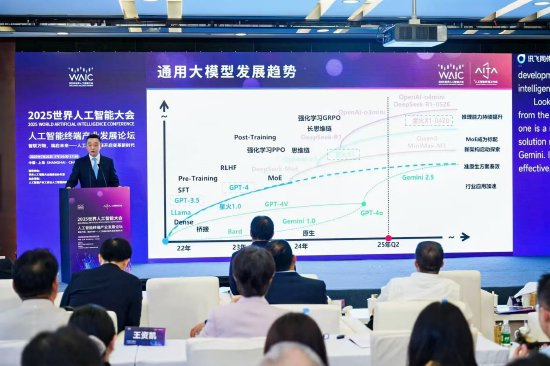




 京ICP备2025104030号-29
京ICP备2025104030号-29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